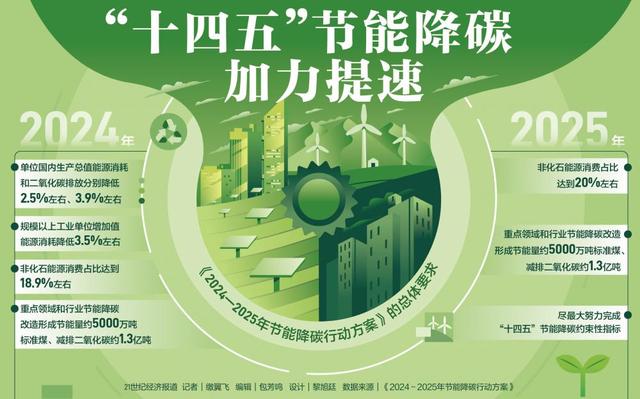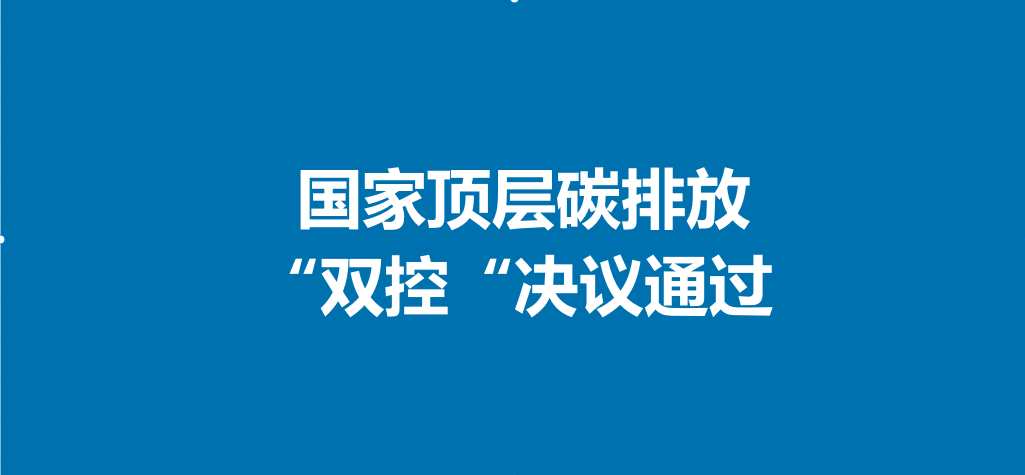国务院关于印发《2024—2025年节能降碳行动方案》的通知
陶澍:农村能源转型应从家庭开始
陶澍:农村能源转型应从家庭开始自发与非自发的转变关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及其影响,目前注意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工业、发电、交通以及城市生活等方面,而对农村用能及污染物的排放则缺乏应有的关注
自发与非自发的转变
关于我国能源结构调整及其影响,目前注意的焦点大多集中在工业、发电、交通以及城市生活等方面,而对农村用能及污染物的排放则缺乏应有的关注。农村生活用能的类型和数量缺乏详细而可靠的追踪记录,导致我们在确定农村地区生活源污染物排放量,分析其对区域大气和室内空气的影响,评估由此导致的暴露和健康效应及制订相应的政策时,都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和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数据,中国大陆农村薪柴和秸秆的消耗量在1992?2012的20年间,仅分别下降了15%和8%。这显然与我们的经验观察和一些已经发表的地方性调查矛盾,也与近20年来农村地区经济和社会快速变化的事实不符。
基于以上原因,在全国几十个单位、一百多名研究人员及数千名大学生志愿者的帮助下,我们调查了1992~2012年间34489个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的能源消费结构和1670个农村家庭的燃料日消费量。调查结果发现,在这20年间,我国大陆地区农村家庭薪柴和秸秆的消耗量分别下降了63%和51%;与此同时,电、液化气和沼气在烹饪用能源消费中的比重从8%上升到了59%,取暖用电比重从2%增加到15%。增幅均在7倍上下,远远超过IEA和FAO数据的10%。
在烹饪用能中,电和液化气的消费比重分别从1992年的3.5%和5.1%上升至2012年的34%和24%,而薪柴和秸秆的比重分别从47%和33%下降至20%和14%。这一变化背后的主要驱动力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我们的研究中,仅人均年收入这一项指标,就可解释近88%的变化。
就转型路径而言,农村地区取暖用能基本遵循“生物质燃料—煤—电”的演化轨迹,这与传统的能源阶梯理论是一致的。但烹饪用能的变化则不同,很多地区跨越了煤这一阶段,直接从传统生物质直接转向了电和液化气,究其原因,仍然要归因于20年间农村地区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导致烹饪用能呈现出了跨越性快速转型的特征,也显示出未来农村用能结构调整的潜力。按照我们的初步估算,当农村人均年收入达到15000元的时候,电力和天然气用于烹饪的比例将高达90%,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烹饪用能的清洁化过程可在未来十余年间大致完成。
相较于烹饪用能,取暖用能的转型则呈现出较为复杂的局面。首先,其清洁化和多样化的速度远不及烹饪用能的变化速率。1992年到2012年间,虽然用于取暖的电力消费增长了7.6倍,但由于其初始水平较低,到2012年,电力在整个取暖用能中的比重仅为15%,农村地区的取暖仍然主要依靠煤炭和生物燃料。事实上,2012年电取暖的农村居民主要分布在取暖时间较短且无需固定取暖设施的中部地区。
此外,取暖用能转型呈现很强的路径依赖,没有呈现出烹饪用能那样的“跨越性”特征。这主要是因为电和天然气取暖成本太高,也与基础设施建设条件(如供电功率)限制有关。导致过去20年间农村地区取暖用能的调整速度很慢。
此外,作为从能源转型的主要驱动力,人均收入与取暖用能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系,且受到其他因素的显著影响。这些因素仍需要进一步研究。从目前获得的数据看,如果没有政府的强力干预(如目前在26+2实施的煤改电和煤改气),农村地区取暖用能在短期内不会出现像烹饪用能那样的自发转型。
需要关注的,不止是煤炭
能源消费结构调整带来的最显著变化是农村地区大气污染物排放量下降。1992到2012年间,因农村地区家庭用能导致污染物、特别是不完全燃烧产物(如一次PM2.5、黑炭和多环芳烃等)的排放量下降了49%~57%。
农村使用固体燃料(煤和生物质,后者包括秸秆和薪柴)导致的污染物排放不仅是区域大气污染的重要贡献者,也会直接造成农户居室室内空气的严重污染,且其污染程度远高于不使用固体燃料的居民家庭。因此,农村家庭用能转型导致的污染物排放下降有着重要的双重意义,一方面对区域空气质量的改善有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可以大幅度改善农村居民室内污染,因此具有重要的健康效应。事实上,长期以来,人们对使用固体燃料造成的农村室内空气污染重视不够。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我国每年由于空气污染导致百万以上人口的过早死亡,其中使用固体燃料造成的室内空气污染的贡献高达40%左右。
近年来,我们在多处农村地区实地测定了室内空气主要污染物浓度,部分地区的污染程度触目惊心。比如,在华北某户家庭厨房中测得的苯并芘日均浓度高达49-548纳克/立方米,卧室中也高达31-187纳克/立方米,而作为一种强致癌物,苯并芘的国家室内空气标准为1.0纳克/立方米。再如,在西部某地冬季测得的居民24小时呼吸PM2.5浓度在70~1650微克/立方米之间,不低于重污染大城市的暴露水平。
目前,农村污染物排放的绝对值虽然有所下降,但其对所有源污染物排放总量的贡献依然很高,尤其是黑炭、有机碳和苯并芘等不完全燃烧产物更是如此。将来依然需要从烹饪和取暖两个方面入手,继续推动能源转型和减排工作。
尽管烹饪用能的转型自发性程度较高,但政府和社会仍可以采取措施加快这一进程。如政府可以结合美丽乡村建设,参照早年“家电下乡”的方式,大力推广电磁炉、电饭锅以及目前农村很少使用的微波炉,同时可以结合精准扶贫工作,采取适当补贴的方式推广使用液化天然气,这些措施可以大大提高农村烹饪用能转型的速度,投入的成本不会很高且可控。
相比之下,取暖用能转型方面的难度要大得多。由于用电和用气的成本超越了目前大多数农村家庭的经济水平,因此需要政府的前期投入。可以预料,这一投入带来的回报将是巨大的。就控制污染物排放而言,生活煤改气的成本效益要显著高于电厂煤改气。燃煤电厂可以通过终端控制减少排放,但家庭炉灶由于燃烧效率低,且没有净化装置,因此单位煤炭消耗量的污染物排放量往往是工业和电厂的数十倍(如二氧化硫)、数百倍(如黑炭)甚至上千倍(如苯并芘)。
另外,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农村取暖用能并不仅仅是散煤问题。根据我们的调查,2012年,农村地区用煤取暖的比例为46%,同期薪柴等生物质的使用比重也高达38%,与用煤比例没有很大差别。因此,应当将关注点从改“散煤”拓展到改“固体燃料”。
技术需接受非技术的挑战
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以及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农村地区的生活形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表现出了较大的地区差异。因此,针对农村地区的能源消费结构转型,需要开展更多的跨学科研究工作,技术措施要接受社会经济和生活习惯等非技术的考验。
以农村沼气的使用为例,在我们的调查中,农村地区沼气的使用量要比IEA和FAO公布的结果低得多,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一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我们的调查,大多数农村沼气设施处于废弃状态。其原因除维护不当外,还与农村地区散养猪数量大幅度下降有关。随着农村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以及劳动力减少,以户为单位的沼气生产已经很难维系。显然,沼气等能源能否大规模推广,并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需要经济和社会层面的综合考量。
农村地区取暖和烹饪用能的调整,应该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规划综合的整体解决方案,需要全面考虑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政府的财政能力以及电网和天然气管网的承受能力等。有条件的地区可以一步到位,直接改用电或气;无法一步到位的地区,则可以探讨其他过渡方式,如与清洁炉灶相结合的压块生物质燃料取暖。这些方案的推广一方面需要寻求市场机制,另一方面,政府的干预和推动也不可或缺。
另一个超越纯粹技术的问题,是污染物减排与二氧化碳减排。由于两者的来源、影响、减排动因、减排方式、减排效益和减排成本有很大差异,因此不能简单化地相提并论。在目前中国的发展阶段和经济水平下,不加区分地笼统谈减排会导致决策偏差。
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二氧化碳排放主要是发达国家的历史贡献。尽管中国目前是第一排放大国,但由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主要还是来自历史排放,目前和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对全球大气二氧化碳增加的贡献大约在10%左右。中国应当承担起相应责任,但没有必要为发达国家的历史排放买单。与此同时,污染物排放导致严重的健康危害,减少污染物排放则应当是我国减排政策的优先目标。
大多数情况下,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减排的方式和效果并不一致。如电厂除尘脱硫、家庭炉灶转型、汽车尾气减排等都是针对污染物排放的,可以降低大气污染程度,但不会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另一方面,诸如碳捕捉和碳存储这样的措施能够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但对污染物减排没有作用。前者对保护我国居民健康有利,后者则在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贡献。当然,有些情况下两者是可以并重的。譬如,清洁能源,如光伏、水电、风电的发展,可以导致污染物和二氧化碳同步减排。再如,不同源的黑炭减排,同样具有双重效应。因此,如何确定减排路径,要明确减排目的,针对我国国情确定优先次序,做好前期成本效益分析,确定最佳减排途径,切忌不区分目的和不计成本的粗放管理策略。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而言,在面对每年大气污染造成百万以上过早死亡的威胁时,大气污染物减排应当放在绝对优先地位。至于气候变化应对策略,则应当将重点放在应对和适应。相关研究的重点也应当如此。
如上所述,在综合考虑技术、经济性和社会效益的前提下,有些情况是可以获得双重收益的。其中生活源黑炭排放的削减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黑炭不仅是危害健康的颗粒物的主要成分,同时也是重要的气候强迫因子。通过减少农村生活源固体燃料的使用,可以大幅度减少黑炭的排放,获得环境和气候的双重效益。
从这个角度看,农村生活用能的调整,确实值得引起更多重视。(文/陶澍)
上一篇:中国实现“无特色、不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