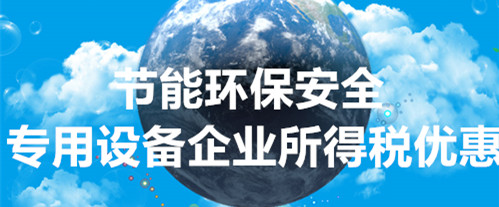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的
首页 > 88betway88
城市史话|黄冈、苏轼与瘟疫
来源:
网
时间:2024-08-19 23:35:59
热度:113
城市史话|黄冈、苏轼与瘟疫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位于湖北省东部、距离武汉78公里。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数,仅次于武汉(截至2020年1月30日12:14,黄冈
黄州,今湖北黄冈市,位于湖北省东部、距离武汉78公里。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当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病例数,仅次于武汉(截至2020年1月30日12:14,黄冈市确诊496例,死亡12例,治愈5例)。
公众眼里的黄冈标签,一是苏轼苏东坡,二是黄冈秘卷。如今又多了一样。
元丰二年(1079 年)十二月,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那年他四十四岁。
元丰二年的元月壬日,苏轼尚还能意气风发地和雷胜(陇西人,京东第二将,臂力惊人,骑射敏妙)等十人狩猎徐州城南,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韵作诗(《苏轼年谱》卷十八“元丰二年”),还特意作了《猎会诗序》来记录这件事,“……客皆惊笑乐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润风和,观者数千人”。(《苏轼文集》卷十)可以说是一桩值得记录的乐事了。
有时世事变幻便是如此。公元2020年和公元1079年并无差别,前一刻还意气风发大笑挽弓,后一刻便风云突变心态颓唐。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上《湖州谢表》,其中“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给自己招来祸事。七月二十八日,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被中使皇甫遵“勾摄”至御史台。八月十八日,赴御史台狱;十二月二十六日,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城赴任黄州。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上谢表。后人评论此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东坡黄州谢表》)黄州在熙宁之后便属淮南西路,治黄冈,县三:黄冈、黄陂、麻城。黄州之名最初出于隋代,后来被称为齐安,到唐代称为黄州,到了宋代得以固定下来。
冬天的黄州气温与今日无异,据苏轼自己描述:“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 (《与章子厚书》)他先是住在黄冈县东南的定慧院,定慧院杂花满山,却有海棠一株,诗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雨中有泪亦悽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分明是说他自己。在定慧院,他还写下“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经历大劫难、初到偏僻之地的苏轼,心情可见一斑。
刚到黄州的苏轼,如同当今的湖北乡亲一样,人皆畏避,唯恐与他交往牵连到自己,日子过得不可谓不艰苦。起初他担心自己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确实如此。他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每月他会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需要取用时便用画叉挑取一块,然后用大竹筒储藏那些没用完的钱以待宾客——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宾客。他天真地盘算了一下,自己的钱够用一年多,那怎么办呢?经过一轮盘算之后,似乎应该为贫困潦倒而悲泣的苏轼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反正够用一年啊,到了那时候我还可以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看看,没什么好操心的!(《答秦太虚书》)
哀怨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苏轼开始操心寻找美食,当地特产江鱼、竹笋、猪肉……他都饶有兴致地予以尝试,并严肃地撰写《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元丰四年(1081),苏轼开垦东门外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将其命名为黄州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山间,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元丰五年,他在东坡筑屋,其时飘雪,遂命名为东坡雪堂。在黄州他看似一无所有,却又迎来了人生转折。《定风波》、《前、后赤壁赋》均创作于这个时期,境遇的大开大合,开启或是印证了他豁达的副本,一开始的忧闷一扫而空,从此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元丰三年,黄州遭遇了一场大疫。本无处事权、自身难保的苏轼惦念当地百姓,用圣散子方予以治疗,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他提及,自古论病,以伤寒最为危急,以圣散子方来治疗,尤为有效。此方他是从老乡巢谷处求得,本答应了巢谷不以此方传人,但还是将其传给了蕲水人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附了此方。并有《圣散子方》一卷流传, 以后被收入《苏沈良方》中。
元丰三年至七年,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同样遭遇了一场大疫,足见这场疫情不止局限在黄州一处,而苏轼也将圣散子方授予了他亲爱的子由。“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 (《雍正江西通志》卷60《名宦四》)当时的人同样是禁止往来,因为内心惶恐而求助于巫卜,苏辙采取的方法也是多制圣散子和糜粥,遍谒病家予之,所活无数。
数年后转知杭州的苏轼又碰到过一起疫情。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这次苏轼同样用了圣散子方救了数千人(苏轼《圣散子方后序》)。然而圣散子方在后世的几次使用中出了差错,根据叶石林《避暑录话》记载:“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此次疫情当是金兵围攻汴京之后造成的大疫,据《宋史·五行志》:“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以及,明代某次瘟疫,根据俞弁《续医说》记载,明弘治癸丑年的吴中大疫因为用了圣散子方,“十无一生”。
药方疗效是另一个领域的话题(常理推断:疫病不止一类,地方水土亦有不同)在此不予展开。说回到作为地方官员的苏轼采取的政策。
在杭州治理疫情的苏轼,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向朝廷请示,诏免本路上供的米的三分之一,稳定了米的价格;二是得了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上百,换成米来救助饥民;三是到第二年的春天,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这三个措施缓解了饥民的困顿局面。苏轼还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坊治病。在处理当前棘手的问题之余,苏轼清楚地意识到,杭州是水路交凑之重地,因此因疫病死亡的人比他处要多。他收集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自掏腰包拿出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病坊”——可以认为是传染病医院,并储备钱粮来提前防备疾病(《宋史《苏轼列传》、韩毅《宋代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当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开始广泛传播,疾病便升级成了瘟疫。瘟疫作为一种统称,包括伤寒、疟疾、痢疾、鼠疫、麻风病、肺结核等等。瘟疫在历朝历代并非罕事。根据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的研究,在春秋至清朝之间的近两千年间(770BC~1911AD),平均四年就有一年会发生疫灾。而疫灾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从大气候看,寒冷期往往是疫灾频繁发生的时期,温暖期疫灾较为稀少。从季节看,以北宋时期为例,一共59个疫灾年份,疫灾平均每2.85年发生一次,夏季和春季为多发期,主要因为夏季温度高、利于细菌滋生,而春季饥荒多发的缘故。在当时疫情多发于首都汴京周边和人口密集的长三角地区(龚胜生《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传染病的传播与气候、时令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古人喜欢把传染病的起因纳入“气”的理论体系里。《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六气分治。”这“六气”指的是风、热、湿、火、燥、寒六种气候分治四时。曹植《说疫气》:“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当玄乎的,似乎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指代的,从天地间穿入人体内五脏六腑的,“气”,和传染病联系在一起后,“气”更偏向于指代气候。气候应该按照规律变迁,不按规律乱来会容易产生疫病。“气”也可是人呼出纳入的气,它无孔不入,弥漫于四周而容易传播。
正因为因气而生,因气而散,治疗也是要提升自身的气,用自身的浩然正气来驱散疾病——可以说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卫生工作也要改善环境中的气——可以说是增强空气流通?似乎也说得通。
瘟疫爆发时期,民众通常会想象,有一种弥漫的圣水或者火来驱散那股邪气,以及最高阶的武器——人的德行。此德行不仅是人自身的浩然正气(免疫力),也是治理者的管理能力(于赓哲《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
苏轼的气镇住了瘟疫的气。“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轼,出得世亦入得世,能烹猪肉,能躬耕田园,逆境与顺境皆不移其志,这是在困境中见天地、见自己、见苍生的苏轼;自身难保之时还不忘民生,开药方救人无数,做起地方官来思路清晰、措施得当,既能务实操作,又能目光长远防患于未然。为官一方便尽忠职守造福一方,这便是千年前黄州及杭州大疫中称职的地方官苏轼。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贬居黄州的第三年。这年的寒食节,他留下了闻名于世的《寒食帖》。那时的黄州依然阴雨绵绵,和今天没什么差别。湖北的雨天总是如此,小雨淋漓不尽,阳光失了踪,湿气深入骨髓,一年复一年,从冬天点滴渗到春天。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光,人生跌入谷底似乎不见天日。当我们望着窗外的雨,想着不知道何时会结束的倒霉光阴时,不如想想苏轼。总有一天,料峭的春风会吹醒今日颓唐的酒,那时山头斜照相迎。坚持,熬过当下病痛的日子、流浪的日子、蛰居的日子、恐惧的日子、为所爱之人牵挂的日子,回首之时,我们也会像躬耕黄州东坡时的苏轼那样,道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到那时,不妨按照他的菜谱烹一锅东坡肉吧。
【宋】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答秦太虚书》:“初到黄,廪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公众眼里的黄冈标签,一是苏轼苏东坡,二是黄冈秘卷。如今又多了一样。
元丰二年(1079 年)十二月,苏轼受乌台诗案影响,被贬黄州,任黄州团练副使。那年他四十四岁。
元丰二年的元月壬日,苏轼尚还能意气风发地和雷胜(陇西人,京东第二将,臂力惊人,骑射敏妙)等十人狩猎徐州城南,以“身轻一鸟过,枪急万人呼”为韵作诗(《苏轼年谱》卷十八“元丰二年”),还特意作了《猎会诗序》来记录这件事,“……客皆惊笑乐甚。是日小雨甫晴,土润风和,观者数千人”。(《苏轼文集》卷十)可以说是一桩值得记录的乐事了。
有时世事变幻便是如此。公元2020年和公元1079年并无差别,前一刻还意气风发大笑挽弓,后一刻便风云突变心态颓唐。
元丰二年三月,苏轼自徐州移知湖州,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上《湖州谢表》,其中“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给自己招来祸事。七月二十八日,上任仅三个月的苏轼,被中使皇甫遵“勾摄”至御史台。八月十八日,赴御史台狱;十二月二十六日,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元丰三年正月初一,苏轼离开京城赴任黄州。二月一日,苏轼到达黄州,上谢表。后人评论此谢表“悔而不屈,哀而不怨。”(《清容居士集》卷四十六《跋东坡黄州谢表》)黄州在熙宁之后便属淮南西路,治黄冈,县三:黄冈、黄陂、麻城。黄州之名最初出于隋代,后来被称为齐安,到唐代称为黄州,到了宋代得以固定下来。
冬天的黄州气温与今日无异,据苏轼自己描述:“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 (《与章子厚书》)他先是住在黄冈县东南的定慧院,定慧院杂花满山,却有海棠一株,诗道:“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雨中有泪亦悽怆,月下无人更清淑。先生食饱无一事,散步逍遥自扪腹。不问人家与僧舍,拄杖敲門看修竹。”分明是说他自己。在定慧院,他还写下“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飘渺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醒。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经历大劫难、初到偏僻之地的苏轼,心情可见一斑。
刚到黄州的苏轼,如同当今的湖北乡亲一样,人皆畏避,唯恐与他交往牵连到自己,日子过得不可谓不艰苦。起初他担心自己一家人吃不饱穿不暖——确实如此。他在给秦观的信中写道,每月他会取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需要取用时便用画叉挑取一块,然后用大竹筒储藏那些没用完的钱以待宾客——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着宾客。他天真地盘算了一下,自己的钱够用一年多,那怎么办呢?经过一轮盘算之后,似乎应该为贫困潦倒而悲泣的苏轼下了这么一个结论:反正够用一年啊,到了那时候我还可以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看看,没什么好操心的!(《答秦太虚书》)
哀怨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接下来,苏轼开始操心寻找美食,当地特产江鱼、竹笋、猪肉……他都饶有兴致地予以尝试,并严肃地撰写《猪肉颂》:“净洗铛,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贱如泥土。贵者不肯吃,贫者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元丰四年(1081),苏轼开垦东门外荒地数十亩,买牛一具,躬耕其中,将其命名为黄州东坡,自称“东坡居士”,与田夫野老相从于溪山间,日子过得津津有味。元丰五年,他在东坡筑屋,其时飘雪,遂命名为东坡雪堂。在黄州他看似一无所有,却又迎来了人生转折。《定风波》、《前、后赤壁赋》均创作于这个时期,境遇的大开大合,开启或是印证了他豁达的副本,一开始的忧闷一扫而空,从此是“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是“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是“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是“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元丰三年,黄州遭遇了一场大疫。本无处事权、自身难保的苏轼惦念当地百姓,用圣散子方予以治疗,所全活者不可胜数(《东坡全集》卷34《圣散子叙》)。他提及,自古论病,以伤寒最为危急,以圣散子方来治疗,尤为有效。此方他是从老乡巢谷处求得,本答应了巢谷不以此方传人,但还是将其传给了蕲水人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在著作《伤寒总病论》中附了此方。并有《圣散子方》一卷流传, 以后被收入《苏沈良方》中。
元丰三年至七年,和苏轼同期遭遇贬谪的苏辙,在任监筠州(治今江西高安)盐酒税期间,同样遭遇了一场大疫,足见这场疫情不止局限在黄州一处,而苏轼也将圣散子方授予了他亲爱的子由。“时大疫,乡俗禁往来动静,惟巫祝是卜。” (《雍正江西通志》卷60《名宦四》)当时的人同样是禁止往来,因为内心惶恐而求助于巫卜,苏辙采取的方法也是多制圣散子和糜粥,遍谒病家予之,所活无数。
数年后转知杭州的苏轼又碰到过一起疫情。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大旱,饥荒瘟疫并作。这次苏轼同样用了圣散子方救了数千人(苏轼《圣散子方后序》)。然而圣散子方在后世的几次使用中出了差错,根据叶石林《避暑录话》记载:“宣和后,此药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此次疫情当是金兵围攻汴京之后造成的大疫,据《宋史·五行志》:“金人围汴京,城中疫死者几乎半数。”以及,明代某次瘟疫,根据俞弁《续医说》记载,明弘治癸丑年的吴中大疫因为用了圣散子方,“十无一生”。
药方疗效是另一个领域的话题(常理推断:疫病不止一类,地方水土亦有不同)在此不予展开。说回到作为地方官员的苏轼采取的政策。
在杭州治理疫情的苏轼,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向朝廷请示,诏免本路上供的米的三分之一,稳定了米的价格;二是得了赐予剃度僧人的牒文上百,换成米来救助饥民;三是到第二年的春天,减价出售常平仓的米。这三个措施缓解了饥民的困顿局面。苏轼还做了很多粥和药剂,派人带着医生分坊治病。在处理当前棘手的问题之余,苏轼清楚地意识到,杭州是水路交凑之重地,因此因疫病死亡的人比他处要多。他收集了多余的钱二千缗,又自掏腰包拿出黄金五十两,建造治病场所“病坊”——可以认为是传染病医院,并储备钱粮来提前防备疾病(《宋史《苏轼列传》、韩毅《宋代地方官吏应对瘟疫的措施及其对医学发展的影响》)。
当一种有传染性的疾病开始广泛传播,疾病便升级成了瘟疫。瘟疫作为一种统称,包括伤寒、疟疾、痢疾、鼠疫、麻风病、肺结核等等。瘟疫在历朝历代并非罕事。根据华中师范大学龚胜生教授的研究,在春秋至清朝之间的近两千年间(770BC~1911AD),平均四年就有一年会发生疫灾。而疫灾与气候变化关系密切,从大气候看,寒冷期往往是疫灾频繁发生的时期,温暖期疫灾较为稀少。从季节看,以北宋时期为例,一共59个疫灾年份,疫灾平均每2.85年发生一次,夏季和春季为多发期,主要因为夏季温度高、利于细菌滋生,而春季饥荒多发的缘故。在当时疫情多发于首都汴京周边和人口密集的长三角地区(龚胜生《北宋时期疫灾地理研究》、《中国疫灾的时空分布变迁规律》)。
传染病的传播与气候、时令有着很大的相关性,因此古人喜欢把传染病的起因纳入“气”的理论体系里。《素问·至真要大论》说:“六气分治。”这“六气”指的是风、热、湿、火、燥、寒六种气候分治四时。曹植《说疫气》:“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当玄乎的,似乎包罗万象无所不能指代的,从天地间穿入人体内五脏六腑的,“气”,和传染病联系在一起后,“气”更偏向于指代气候。气候应该按照规律变迁,不按规律乱来会容易产生疫病。“气”也可是人呼出纳入的气,它无孔不入,弥漫于四周而容易传播。
正因为因气而生,因气而散,治疗也是要提升自身的气,用自身的浩然正气来驱散疾病——可以说是增强自身免疫力?卫生工作也要改善环境中的气——可以说是增强空气流通?似乎也说得通。
瘟疫爆发时期,民众通常会想象,有一种弥漫的圣水或者火来驱散那股邪气,以及最高阶的武器——人的德行。此德行不仅是人自身的浩然正气(免疫力),也是治理者的管理能力(于赓哲《弥漫之气:中国古代关于瘟疫“致”与“治”的思维模式》)。
苏轼的气镇住了瘟疫的气。“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园乞儿,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的苏轼,出得世亦入得世,能烹猪肉,能躬耕田园,逆境与顺境皆不移其志,这是在困境中见天地、见自己、见苍生的苏轼;自身难保之时还不忘民生,开药方救人无数,做起地方官来思路清晰、措施得当,既能务实操作,又能目光长远防患于未然。为官一方便尽忠职守造福一方,这便是千年前黄州及杭州大疫中称职的地方官苏轼。
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苏轼贬居黄州的第三年。这年的寒食节,他留下了闻名于世的《寒食帖》。那时的黄州依然阴雨绵绵,和今天没什么差别。湖北的雨天总是如此,小雨淋漓不尽,阳光失了踪,湿气深入骨髓,一年复一年,从冬天点滴渗到春天。
每个人都会经历这样的时光,人生跌入谷底似乎不见天日。当我们望着窗外的雨,想着不知道何时会结束的倒霉光阴时,不如想想苏轼。总有一天,料峭的春风会吹醒今日颓唐的酒,那时山头斜照相迎。坚持,熬过当下病痛的日子、流浪的日子、蛰居的日子、恐惧的日子、为所爱之人牵挂的日子,回首之时,我们也会像躬耕黄州东坡时的苏轼那样,道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
到那时,不妨按照他的菜谱烹一锅东坡肉吧。
【宋】苏轼《寒食帖》,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临江仙•夜归临皋》:“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答秦太虚书》:“初到黄,廪入既絶,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度囊中尚可支一岁有余,至时别作经画,水到渠成,不须顾虑,以此胸中都无一事。”
《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燕脂雪。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
苏伊士在东南亚赢得两项水资源可持续管理合同2019-12-05
-
黔东南州开展新增34个控制单元监测断面摸底调查监测工作2019-11-04
-
目前全球出口的废弃物中约75%最终流向亚洲 东南亚国家强化“洋垃圾”进口限制2019-09-19
-
粤丰环保获授黔东南州南部片区垃圾焚烧发电厂的特许经营权2019-08-05
-
大东南困境求生 诸暨国资取代大东南集团入主上市公司2019-07-19
-
东南亚无力处理洋垃圾 日本将向其出口垃圾发电技术2019-06-27
-
福州市《东南沿海丘陵地区普通公路路域生态环境修复关键技术研究》科研课题项目询价函2019-06-14
-
东南亚拒当“洋垃圾场” “禁废”应有全球方案2019-06-06
-
贵州黔东南州煤矿废水治理一再“缩水” 仍有数千万吨酸性废水直排鱼洞河2019-05-12
-
废弃物能源回收:东南亚的可再生机遇?2019-02-24
-
世界第三钢企将出炉 河钢收购塔塔东南亚70%业务2019-02-02
-
湖州市环境卫生管理处市北片区、东南片区、仁北片区环卫作业一体化服务采购项目的中标结果公告2018-12-27
-
泰国“塑料中毒” 这些东南亚国家急忙封住“垃圾桶”2018-11-05
-
接盘洋垃圾?东南亚国家说不2018-10-30
-
一文了解我国绿色专利申请现状:聚集东南沿海、以高校为主、4大领域占9成2018-09-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