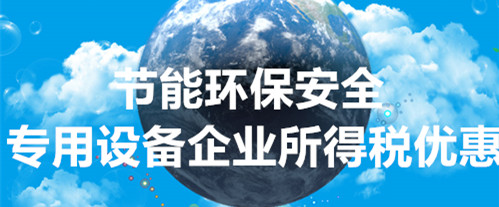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电解铝行业节能降碳专项行动计划》的
深度 | 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
深度 | 拾荒江湖兴衰—北京可回收垃圾的底层真相固废网讯:赵胜是一名流水线上的拾荒者。每天,他紧贴着一条传送带工作,扫视、摸索、拆分,快速从里面分拣出塑料、金属、橡胶等可回收物,扔
固废网讯:赵胜是一名流水线上的拾荒者。每天,他紧贴着一条传送带工作,扫视、摸索、拆分,快速从里面分拣出塑料、金属、橡胶等可回收物,扔进身后的编织袋。
这里是北京阿苏卫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一天要处理5000多吨生活垃圾——相当于北京生活垃圾日产生量的五分之一。近十年来,赵胜所在的明珠洲际科贸有限公司承包着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回收项目,每天承担1600吨-1800吨的分拣量。
赵胜的工作是把垃圾分类做到极致。光是塑料,他就能分出十几种,而且还能分辨哪种更值钱。比如,光是一个饮料瓶,瓶盖、瓶身、包装纸的材质是不同的;拿到一个透明塑料储物箱,要把彩色的把手从箱体上掰下来,两者材质不同,透明的更值钱些。
经历过流水线上的分拣后,挑剩下的垃圾被用来焚烧发电、填埋;而那些拣出来的,将在造纸厂、塑料制品厂、金属制品厂重获新生。
赵胜们来自偏远、贫瘠的乡村,仰赖城市里的生活垃圾维持生计。他们在垃圾桶、垃圾楼、工厂式的垃圾分拣车间里寻寻觅觅,他们中也有一批人,蹬着三轮车,沿街叫喊“收废品喽”。
最鼎盛时,北京拾荒者数量达到17万人。这一群体受到的评价极为两极化:一方面,拾荒者之间的交易未被纳入国民经济系统;另一方面,他们回收的废品量和送往垃圾处理厂的垃圾量相当,为北京省下一半垃圾处理开支。一方面,他们缓解了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另一方面,他们游离于监管之外,在生产、交易中制造环境污染。
在非首都功能疏解、环境整治、垃圾分类等一系列政策的裹挟之下,北京拾荒群体的生存空间愈加狭小。
30多年,宛如浮萍流荡,起落沉浮。拾荒者的前半生,是底层追逐更好生活的写照,也是城市垃圾对策变迁的生动切面。过去,他们因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而出现,未来也必将随着“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缓解而消失。
不变的是,城市和垃圾依旧存在。
从村庄到流水线
那些被人们扔掉的东西,破袋而出,重新在传送带上展露真容。赵胜说,垃圾里有一切你能想到的东西,肮脏的、腐臭的、涉及主人隐私的,也有让人兴奋的,比如大叠大叠的钞票。

垃圾里捡到钱,是分拣工们津津乐道的事。赵胜的上司老夏说,早年有个分拣工突然离职去做生意,后来他听说,这人从传送带上捡到一个包,里面有几十万元现金。就在老夏向《财经》记者讲述这个未被证实的传闻时,几名分拣工附和过来,分别说起他们熟知的其他版本的分拣工捡钱致富故事。不一样的时间、人物、数额,却有着同一种功效——足以激励平凡岗位上的他们分得更仔细、拣得更有劲。
就连不怎么进分拣车间的老夏,也交过一次好运。几年前,老夏在车间检查,瞧见传送带上一件衣服口袋鼓鼓囊囊的,下意识拿过来翻了翻,里面塞着一叠钱,回去一数,整整7900元。不过现在,这种好运越来越罕见了。分拣工们归纳出两个原因:电子支付逐渐取代了传统的现金交易,纸钞用得少也丢得少了;反腐败卓见成效,往垃圾桶丢巨款的贪官少了。
对赵胜来说,脏没什么不能忍受的,“反正这个皮带,一下子就过了,脏的(东西)又不伤手”。
更大的挑战是气味。
垃圾分拣车间大门紧闭。如果没有要紧事,管理层不愿轻易推开这扇门。里面弥漫着一种类似臭苋菜的味道,浓稠的气味非常霸道,一旦粘上衣服,掸也掸不去。“进去走一下,就算马上出来,我也要换身衣服。”一名管理层员工说。
赵胜的家乡位于四川巴中。山村里交通和经济都不发达,也没有一家企业。赵胜在家带孩子,偶尔做点农活儿。
2012年春节,觥筹交错间,一位从北京回来的老乡说起,在北京捡垃圾不错,一个月能挣四五千。25岁的赵胜备受鼓舞,过完年,他带着妻子来到北京,成为垃圾分拣流水线上的两个小蓝点。
和赵胜一样,他现在的领导——巴中人许际才的命运转折点也出现在25岁。1986年,许际才月入不到30元。一位姓雷的老乡告诉他,上北京捡破烂,一天就能挣30元。
许际才说,老雷回北京那天,什么都没带,就带上了自己家的三兄弟。他也很想去北京闯闯,像老雷一样月入900元,于是恳求老雷:“把我也带上呗。”
一张12.5元的火车票,把他送到北京。来自钢铁企业的废材,有铁也有水泥,用个锤子把里面的铁剃出来,废铁能卖二毛五一斤。一天下来,许际才果真能挣到二十几元。
“我们那个时候相当苦。”许际才说,刚到北京时,没有固定住所,用块塑料布蒙住被子,和锅一起随身带着。白天到处捡废品,走到哪里,晚上就在哪里休息。
偶然的机会,寄居粪库的许际才遇到一位下来调研的官员。这人是王维平,当时在北京市环卫局工作,负责管垃圾场。王维平回忆,看到数九寒天住在粪库里的许际才,觉得他特别可怜。
1988年,许际才和另一名巴中人辗转找到王维平,说想去垃圾场捡垃圾,请他帮忙写条子。王维平答应了。
“当时我没有什么循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仅仅出于怜悯之心,觉得这些人不容易。另一个考虑就是,你捡得越多我越省钱,就不用去花钱焚烧了。”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
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北京就成立了国营的废品回收公司。到上世纪70年代,二环路内出现2000多家废品回收站,几乎每个胡同都有。
“但是自打许际才他们一进京,迅速地把这支队伍给击垮了。”王维平说,拾荒群体的优势在于不怕丢人,背着一个破口袋,一个垃圾桶一个垃圾桶翻。废品回收公司的正式职工不会这么做,出于面子,也有体制上的原因——不管回收多少废品,月薪都是固定的。
在城乡发展不平衡的背景下,四川巴中、河南固始的农民受到高收入诱惑,前赴后继涌向北京。一如现下蜂拥而去BAT等技术密集型企业的城市白领们。
往后数年,北京拾荒群体数量迅猛增长。据王维平撰写的《北京垃圾回收及产业化调研报告》称,20世纪末,在北京拾荒的外来人口有8.2万,其中约4.6万来自四川,约1.7万来自河南,约1万来自河北,约1700人来自江苏。
拾荒江湖滋生出大量恶性事件。1996年,许际才等人又找到王维平,说了两件事。首先是自称因王维平帮忙写条子进垃圾场而“发了大财”,想要报恩。第二桩是,北京垃圾回收市场竞争日趋激烈,以拾荒者户籍不同分成了13个帮派,这些帮派甚至有各自的“武装”,为争夺地盘,每年都有打架、斗殴等事件发生,还有人为此丧生。他们想借助王维平的力量为四川帮“扩大地盘”。
“我当时就萌生了调查这支队伍的想法。”王维平告诉《财经》记者,几天后,他召集各个帮派负责人聚餐,想要调查各帮人数、盘踞地点、主要营生及人均收入。
王维平说,为减少恶性事件,他给各个帮派分了工:四川人捡垃圾(小区垃圾桶、垃圾中转站、填埋场、处理厂),河南人收废品,河北人在四环路外接应负责向外运输再加工,江苏人则主要搞泔水和地沟油。这一拾荒格局延续至今。
焚烧不是最好的选择
呼之欲出的垃圾分类立法,让流水线上的拾荒者认为,月入四五千的好日子马上就要到头了。
继上海开展强制垃圾分类后,北京的垃圾分类立法工作也已经提上日程。《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修订在即,草案预计10月提请市人大常委会一审。
王维平说,目前,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已进入减量化、资源化阶段,而垃圾分类正是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措施之一。
就像排斥电子支付在取代现金支付一样,流水线上的拾荒者也对垃圾分类感到反感。他们担忧的是,垃圾分类后,送到末端的就只剩下不可回收垃圾了。那么,垃圾分拣流水线便没有存在价值了,他们也将面临失业。
“大不了不干这一行了,不挣这么多钱了。”赵胜说,他还年轻,随时可以在城市里找到其他工作。
54岁的徐治新没这么乐观。他和妻子是“非典”后来北京的,刚开始在填埋场附近捡垃圾。一个月下来,两人能有8000元-9000元收入。他认为这份收入还不错。曾有人找徐治新去填埋场种树,他给拒绝了,“搞绿化挣不了多少钱,一般也就3000块钱。”
2009年,徐治新成为许际才手下。他在流水线上做过分拣工,也开过铲垃圾的铲车,前后工资变化不大。徐治新说,要是分拣项目没了,年轻人还可以出去创业,但像他这个年纪,就很难找到新工作了。
拾荒者的沉浮起落,是北京垃圾对策变迁的一个切面。
王维平说,北京的生活垃圾对策是个四部曲,先后经历了“眼不见为净”时期、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期、焚烧时期、减量化和资源化时期四个阶段。拾荒者的身影贯穿始终。
第一阶段,北京把生活垃圾运往郊区,“随便找个地方堆起来,简而言之就是眼不见为净”。久而久之,垃圾就围城了。北京市在1983年做过一次航拍,大致沿着现在的四环路一圈,仅50平方米以上的垃圾堆就有4700多个。
随着北京申办亚运会、奥运会,城市摊大饼似的发展到了四环。这时候,北京开始建设垃圾填埋场、垃圾收集运输体系。之后,生活垃圾被运到垃圾填埋场,“找个坑就填”。
不管是堆起来还是填起来,都会污染地下水,周围臭气熏天,同时还产生大量甲烷——其温室效应是二氧化碳的21倍。
彼时,拾荒者的大本营,大多驻扎在垃圾堆放场周围。1997年,王维平曾挨个去13个帮派的大本营调研,周末就和拾荒者住在一起。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难闻的气味。难闻到什么地步?大本营里冬天都有苍蝇。不管是那的蟑螂还是绿豆蝇,个头都很大,一点也不像北方常见的。
三九天,饭碗一捧,一层大绿豆蝇就在上面趴着、围着,王维平把它们扇开,马上又聚拢回来。
随着填埋场建成,拾荒者聚集到了填埋场附近。不过,由此产生的隐患也很多。汽车卸垃圾,来回冒土扬烟,偶有意外伤人事故发生。
第二阶段,是标准化垃圾填埋场时代。“标准化”是指把填埋场的危害降到最低,具体做法是:填埋场下铺设七层防渗措施,防止地下水污染;分区填埋,倾倒的垃圾当天压实、盖土;把填埋场产生的甲烷倒排出来,用于集中发电;对填埋场的污水进行处理。
国际上,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采用标准化垃圾填埋场。1994年中国首座标准化垃圾填埋场,也就是位于北京市昌平区的阿苏卫垃圾填埋场建成投产。
新对策没有彻底解决矛盾。首先,防渗膜的有效期为12年,过期后,还是会污染地下水;第二,填埋场产生的甲烷仅有一半能被有效收集;第三,填埋场占用大量土地,一旦填满垃圾,很难重新被利用。王维平说,这种土地上,盖房子地基不牢,绿化也不行,堆体里不断发热,树种了就烧根。
第三阶段,以焚烧为主的多样化末端处理方式。当北京计划建造第一座垃圾焚烧厂,也就是阿苏卫生活垃圾焚烧厂时,遭到了民间反对。据王维平回忆,2009年,全国多地出现抗议垃圾焚烧的示威游行。反对者认为,焚烧是把固体污染转化成气体污染。
当时的北京市政府官员让王维平出面和反对者进行沟通。王维平带着反对者去日本参观了垃圾焚烧厂。在日本,垃圾焚烧厂一墙之隔就是幼儿园。“参观过程中,他们慢慢了解到,垃圾焚烧的核心技术是烟气净化,有60%的投资花在烟气净化上。净化到什么程度呢?比烧油的炉子、烧煤的炉子都干净。”王维平说。
也正是这一年,许际才承包下阿苏卫的生活垃圾分拣、回收项目,进入了城市生活垃圾的末端分拣行业。他招了100多位拾荒者来当分拣工,行情好了,多招一些,行情不好了,少招一些。
截至2019年2月,中国(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在运行的生活垃圾焚烧厂数量已经突破400座。王维平认为,垃圾焚烧还不是处理垃圾的最理想方式,垃圾对策的上策是第四个阶段——减量化、资源化阶段。
他给出了三个理由。第一,垃圾焚烧厂即便能克服“人类一级致癌物”二英,但产生的一氧化碳、二氧化碳、氮氧化物、硫化物等还是存在污染。第二,焚烧的产物之一飞灰属于危险废物,处置过程中暴露很多问题。第三,焚烧厂的炉渣率有23%,大部分最后还是要填埋。
断裂的回收链
早上7点不到,李军一家驾驶两辆货车,从居住的西六环出发,开向北京石景山。他们将在一个小区外支起摊位,迎接附近居民,也迎接骑着三轮车来送货的、更下游的废品回收者。
李军回收各式各样的废品。每天最多能收2吨纸、1万个矿泉水瓶,还有铁、铜、铝等金属。一年下来,刨除花销,有10多万元收入。在李军看来,这些是辛苦钱,“本地人估计干不了”。
首页 下一页 上一页 尾页-
湖南将建5座餐厨垃圾处理厂 各地都要垃圾分类2019-09-16
-
内江城乡生活垃圾处理PPP项目:17个子项目已开工15个2019-09-16
-
2019年中国垃圾分类发展状况:中转站、回收网点建设的市场规模将超200亿元2019-09-15
-
《生活垃圾处理处置工程项目规范》 (征求意见稿)发布!2019-09-13
-
鄂尔多斯:《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2019-09-13
-
上海“史上最严”垃圾分类已两月 咋样了?2019-09-12
-
46城进入强制垃圾分类“快车道”2019-09-12
-
北控获石家庄市四个区的垃圾分类样板小区建设项目2019-09-12
-
2019年上半年中国垃圾分类政策分析及垃圾分类发展趋势分析[图]2019-09-12
-
四川垃圾分类深度推进 九成行政村已建立垃圾处理机制2019-09-11
-
2019年垃圾分类产业链分析报告 至25年生活垃圾分类服务市场空间达392.43亿/年2019-09-10
-
六地加入垃圾分类行列:奖罚分明、纳入征信动真格2019-09-09
-
沪垃圾分类最新成绩单:干垃圾处置量减少 湿垃圾分出量提高2019-09-09
-
读懂垃圾分类重在细节掌握2019-09-09
-
《福州市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四定”工作实施方案》制定2019-09-08